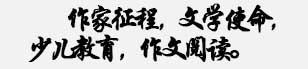散文《待到山花含苞时》
云南省文山州文山市::何源梅 (文山市)
2014年12月24日,是我到文联工作最难忘的日子。民政局通知我去参加散葬烈士迁坟活动,把散葬烈士从荒野搬到文山烈士陵园。
天蒙蒙亮我们就出发了,因为我们要在太阳出来的时候赶到喜古乡,在动土的那一瞬间让烈士的魂魄感受到寒冬里的第一缕阳光。
一路上,民政局的苟峰副局长告诉我说,文山市有64位散葬烈士,都是1937年以来在历次剿匪战斗和清匪反霸中牺牲的,要把他们的坟迁到文山烈士陵园内。我们这次去喜古乡,是为烈士搬家的。
九点钟,我们爬上了被百姓取名为烈士山的山坡上。太阳越来越亮堂,银色的青霜开始融化,从泥土中渗出的露珠,在草尖上开出五角型的花来,是在祭奠烈士,还是送他们一程呢?两者皆是吧,我这样想着。
一位姓孙的大哥扒开杂草覆盖的墓碑蹲下身去。我们看见墓碑上红五星的颜色依旧,只是多了几分风吹雨淋的痕迹。我们对着墓碑作了三个揖之后,点燃三烛清香,燃起三张纸钱,告慰坟里的烈士说:后人为你们建造了一个美丽的家园,今天来为你们搬家了。话音刚落,燃烧的纸钱和清香笑出声来。是王自能烈士笑出的声音,还是张昆烈士的笑声?那是一种含着泪水笑出的声音,这声音让高枝上的鸟儿哽咽,让山下的炊烟弯下了腰,让草尖上的青霜泪水涟涟。
孙大哥用锄头挖开坟土,他用锄头的姿势,很轻很轻,似乎怕打搅睡梦中的英雄。他挖了很深的一个坑,才露出一块腐烂的木块和几块青瓦的碎片,很长一段时辰,才发现几根手骨。之后,那位大哥再怎么刨也找不到其它的骨骼了。他把找到的骨骼捧到红布里,包好,放进木盒子里。
隔壁那座坟墓的主人叫张昆。一位老乡说,张昆烈士牺牲后被抛到山野,待乡亲发现时,只捡到血衣一件。难怪空空的墓穴里,只埋葬着烈士的魂魄。一窝蚂蚁从土里钻了出来,在墓穴里排成长队。它们是在送烈士上路啊!只见一位大哥捧一把墓穴里的泥土放进红布包里,然后扎成英雄花的样子。
一路上,文山烈士陵园的园长李洪斌打开车上的音响,那首《十送红军》的歌凄凉而让人落泪。“五送(里格)红军,(介支个)过了坡,,鸿雁(里格)阵阵,(介支个)空中过…… ”我们跟在灵车的后面,说一声,叔伯啊,快些走吧,不要回头,前面就是你们美丽的新家了。我们用泪水送行我们的父辈,因为他们中没有一男半女,我们就是他们的亲人。
苟峰告诉我说,文山市的60多名散葬烈士,大多数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很多人还没有娶上媳妇,没有听到孩儿喊过一声爹,就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
翻开散葬烈士的名录,我最熟悉的还是农民游击队长周小友烈士。白色恐怖下的1937年,反革命势力十分嚣张,游击队长周小友在乐诗冲被敌人杀害。牺牲时年仅29岁。秉烈区的朱荣海区长,被土匪杀害后抛进深深的落水洞,人们为了记住他,把他曾经用过的一个水杯,一枚五角星当做他的尸骨埋在了高高的山岗上……
翻开文山市零散烈士普查登记表,我的心像雪地里的柿子一样疼痛。因为有的名册上面没有烈士的姓名,没有出生年月,有的连籍贯都找不到,还有的就连简要的事迹都是空白的,而他们牺牲的时间和地点却历历在目。在小街战斗中牺牲的13名无名烈士,只能用编号来排列。
提到烈士这两个字,我的心情特别的沉重,你不知道烈士们有多苦,有的人连一双像样的布鞋都没有穿过;你不知道他们流血的时候有多疼,连身边的一根救命野草都没有抓到;你不知道他们闭上眼睛的一刹那有多累,连喊一声亲娘的力气都没有……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半个多小时后,我们走进肃穆的烈士陵园。我把准备好的三七酒打开,洒在了高高伫立的纪念碑前,我想让这久藏的三七酒为无名的、有名的烈士好好地疗伤,让他们好好地开怀畅饮。那一瞬间,我的泪忍不住流出来。那些孤独的灵魂终于有了新家,我感到心灵中的一份慰藉在疯长。
是啊,如果不是这些将士血洒疆场,我们又怎么能看到发展进步的新文山和人民群众幸福的生活。
青山埋忠骨,桂树含花苞。我从远处摘来几束绿色的万年青,还有几束狗尾草,我把它们敬献在烈士的墓碑前,深切悼念这些短暂而永恒的生命。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此文在2015年云南省作家协会“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征文活动中获奖)
作者简介
何源梅,别名,山妹子,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1999年开始文学创作,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作品在《边疆文学》《含笑花》《云南日报》等报刊发表,多次在省、州征文活动中获奖,著有散文集《山洞月》《百草芊芊结》。组织编辑出版《文化文山》《传说文山》《记忆文山》《传奇文山》等书籍,创作歌曲《醉美君龙湖》,电视散文《天赐神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