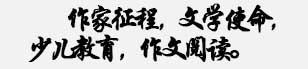《哦,香雪》观后感
云南省文山州文山市:沈小宁
香雪,十七岁, 纯真善良、渴望文明、自尊自爱,平时说话不多,胆子又小的山村少女,偏僻的小山村台儿沟唯一的女初中生,她去公社上学需要行走十五里路,她发现了看到新式铅笔盒。
在火车停站一分钟的间隙里,她想都没想险毅冒险冲上车厢,甘愿被父母责怪,用积攒的一篮子四十个鸡蛋,与铅笔盒的主人女学生交换,换来了一只向往已久的装有磁铁的泡沫塑料自动铅笔盒。 不料火车开动前进离开家乡,直到三十里路外的车站停站下车,她一个人摸黑行走了三十里的山路,回到自己的熟悉陌生的家乡的震撼心灵的小段经历探险体验故事。
表面上写台儿沟一群姑娘的故事,实际上主要写的是中学生香雪,为了心仪已久的铅笔盒而不惜行走三十里夜路的故事。
在火车上,当她红着脸告诉女学生,想用鸡蛋和她换铅笔盒时,女学生不知怎么的也红了脸。她一定要把铅笔盒送给香雪,还说她住学校吃食堂,鸡蛋带回去也没法吃。 女学生怕香雪不信,还指了指自己胸前的校徽矿冶学院。 香雪觉得女学生是在哄她,在她看来,那也可以把鸡蛋拿回家。
香雪和女学生都很淳朴,她们的也都能打动触及读者的内心。
小说开头写出,是因为有了火车,而火车需要的铁轨被铺进了深山,才让山外面的人知道了台儿沟这个小山村。
在一分钟的时间里,姑娘们挎上装满核桃、鸡蛋和红枣大枣的柳条篮,站在车窗下,踮着脚尖,手臂伸得直直的,换回台儿沟这里很少见到的挂面、火柴,甚至是姑娘们喜欢的发卡、香皂、甚至是会挨长辈骂的有机玻璃发卡、夹丝橡皮筋,纱巾,能松能紧的尼龙袜。 她们与坐火车的乘客交换也这样地淳朴。
火车停住时姑娘们心跳着涌上前去,像看电影一样,挨着窗口观望。 陌生的事物面前,香雪躲在后边,双手捂着耳朵更加胆小。对于火车所载来的新的世界,香雪比过其他姑娘们更加执著追求。 看火车香雪总是第一个出门。
姑娘们盼望着的火车来到,又盼又心跳不已。她们对新鲜庞然的火车怀有一些害怕和恐惧等的心情和状态。
姑娘们也会有真诚幼稚的发问,在主要角色香雪身上得到了见证,集中的体现台儿沟的姑娘们的美丽心灵世界。
向往火车以及它带来的新鲜事物的姑娘们懂事可爱,她们几乎个个不失幼稚可笑及话语蹦出来,反而愈加显出她们人性与心灵的淳朴美好,连小说中的列车员小伙子北京话也是深受感染意外惊讶。
姑娘们一眼看见的是妇女头上的金圈圈和腕上比指甲盖还要小的手表,她们更喜爱的是发卡纱巾花色繁多的尼龙袜。
香雪发现行李架上那连小城市都随处可见的棕色人造革学生书包倍感新奇。
五彩缤纷的车厢世界有着喜爱物品,凤娇让香雪去看女乘客头上的时髦发饰手表。
香雪捕捉发现的是人造革学生书包,最重要的敏锐地发现了强烈渴望梦寐以求得到一个能够自动开关的铅笔盒。
香雪心里一直装着这种铅笔盒和它的价值,这是一个宝盒子,谁用上它就能一切顺心如意,就能上大学、坐上火车到处跑,就能要什么有什么,就再也不会叫人瞧不起。
铅笔盒能够满足香雪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深层需求驱使香雪打听自动开关的铅笔盒的价钱。她总是利用买卖的机会向旅客打听,打听北京的大学要不要台儿沟人。
香雪误上火车,实际上是勇敢地上了火车,但因火车仅仅在台儿沟站停留一分钟,才造成了香雪没能下车,怀揣下不了火车的意外惊吓,只能在三十里外的下一站下车,香雪还是在火车上成功换到了那个她心仪已久的自动铅笔盒。
香雪登上火车的一瞬间,不寻常不平凡的一瞬间,车上车下是两个世界,看火车和乘火车是两种身份和两种体验的,她由此开始体验飞驰的速度和感受,开启一段新的人生旅程,产生新的自我主体性。
台儿沟的姑娘们是一个群体,她们有着山村姑娘共有的纯真朴实和善良,以及对美的热爱和隐秘的梦想。
她们的性格与心灵,在对火车与它带来的山外的事物与人们表现出强烈兴趣,以及在用土产从车上的旅客那里换回日常生活用品和用于打扮自己的饰物等行为,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姑娘们的一惊一乍和凤娇与列车员小伙子北京话的对话、拌嘴和朦胧似有若无的情感,都因为是用了台儿沟的姑娘们的视角,尤其是用了香雪的视角,来作第三人称人物有限视角叙述,才会愈加映衬出她们纯洁无瑕的心灵,才会让读者具有能够洗涤现代都市生活自私功利甚至丑陋的人性的力量。 这些姑娘们对美好事物的憧憬,她们对美好未来的遐想,甚至少女情愫初显。
凤娇暗恋上第三节车厢上的那个身材高大,头发乌黑,两条长腿白净的北京话年轻乘务员,从第一次接触到后来的无功利目的的交往,别无所求一厢情愿的情愫,凤娇从中得到了难以言传的情感和心理的满足。 巨大的城乡差别都阻挡不了的坚决而美好的一厢情愿式的爱恋。
城市人的列车员以及北京话的小伙子,他们没有世俗和世故的眼光说话处事对待她们。
香雪走在回台儿沟的路上打开铅笔盒时,她学着同桌的样子轻拍盒盖,没有摸过碰过同学的高级铅笔盒,现在她也成了这样的铅笔盒的主人,她对宝盒开启是一个技艺技术习得的行为过程。
香雪做买卖更为纯净,旅客们爱买她的货,她是那么信任地瞧着你,连价钱都是你看着给吧。 这个女孩子还不知道什么叫受骗。
香雪在对现代文明表现出热爱和追慕,是台儿沟姑娘的领头人和杰出代表。
姑娘们自发形成的一个以物易物的市场,表明她们在创造现代经济生活。
每天停留一分钟的火车,打通了闭塞落后的小山村台儿沟与外面世界的联系,也为香雪和一群山村少女开启了一扇感受现代文明的窗口,唤醒了她们埋藏于心的对爱与美和理想的追求。
作者又用乘客的视角来叙述,你望着她那洁净得仿佛一分钟前才诞生的面孔,望着她那柔软得宛若红缎子似的嘴唇,心中会升起一种美好的感情。
香雪和姑娘们视角的第三人称人物有限视角叙述,使得小说后半部分变得合情合理时有小悬念,最终形成整篇几乎没有戏剧化冲突故事的小说最为高潮的部分。
香雪被火车唤醒,知道自己追求什么,自我确认确证,内化了自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从而形成自我人格和新的自我意识。
在香雪的成长中,登上火车不仅是一个外在心灵的冒险事件。
乘火车对香雪而言是全新的时间空间的一种震惊体验,她进入新的社会结构关系中,成为一个主体全新自我现代意识。
香雪乘火车获得铅笔盒发现风景的同时,风景也对她的认知产生影响。
一个少女在寒风中和寂静的山路上,内心的恐惧可想而知了。
秋日的败草粗糙的树干荆棘怪石以及漫山遍野的树,也照见了香雪手中闪亮发光的铅笔盒。
终于能够想到把它举起仔细端详欣赏了梦寐以求许久得到的自动铅笔盒。
现在,在皎洁的月光下,她才看清了它是淡蓝色的,盒盖上有两朵洁白的马蹄莲。她小心地把它打开,又学着同桌的样子轻轻一拍盒盖,“哒”的一声,它便合得严严实实。 只有这时,她才觉得这铅笔盒真属于她了。
当香雪拿着属于自己的铅笔盒返回台儿沟时,她完成了精神蜕变和思想升华,成为新的主体。
她的眼光变了,她发现大山、、月亮、群山、核桃树核桃叶都美极了。
香雪走着,就像第一次认出养育她成人的山谷。
香雪拔下一根枯草,将草茎插在小辫里,这是娘告诉她的避邪方式,实际上暗示了香雪走夜路的恐惧心理。
有了这避邪的草茎,她向吓人的隧道冲去,迎面出现了一颗颗黑点在铁轨上蠕动,那是迎着她走来的台儿沟的姐妹们。
读者是跟着香雪的视角和目及所见,来辨识和发现她们的。 就是香雪当时最为真实的心理感受和身体感受叙述,可以使得读者产生感同身受的真实感和现场感。
面对来找寻她的姐妹们,香雪流下了欢乐满足的泪水。 劳累惊惧袭扰的香雪用手背抹净眼泪,拿下插在辫子里的那根草棍儿,举起铅笔盒迎着对面的人群跑去。 山谷里回荡着姑娘们欢快地呐喊香雪的名字。
接下来香雪孤身一人走夜路一路的心思涌动和思绪流转,与溪水大山和周围的一切那样地情景交融,也全都是采用香雪的第三人称人物有限视角来叙述,才能将一个少女的担虑欢欣跃然纸上。
回家该怎么解释自己用所有的鸡蛋换回了一个铅笔盒等等,写得那么真实和感人。 让读者也随着她的心理和思绪波澜起伏。因为紧贴香雪的第三人称人物有限视角叙述,才会有这样的细节化叙述。
只有台儿沟的女学生香雪,才会对于自动铅笔盒的这样陌生喜欢和渴望珍惜的心理感受情愫。 连怎么使用都要根据记忆中,同桌怎么用它来尝试使用开合这个铅笔盒。
从首都开来的火车给她带来了机会,她不惜代价地从女大学生手中换来了自动铅笔盒,将改变她的身份进入先进文明的行列,与山外的同学平起平坐。
这是未曾遭到文明撞击带来的屈辱的凤娇们所难以理解。
铅笔盒作为一个文具,自然可以看成知识的象征追求,乡村初中生香雪的铅笔盒有着呼应现代化的历史诉求讲述叙事性,道具意义所不断暗示的还是人性的魅力。
铅笔盒,是香雪的个人需要,是获得尊严实现自我的需要,人物的刻画只能遵循人性的逻辑,香雪的情结就是要洗雪文明的落差带给她的屈辱。
铅笔盒不仅给了香雪巨大的力量,帮助生性胆小的她战胜了走夜路的恐惧,还改变了她对这个世界的感受。
现代文明城市里才有的可以自己关上的塑料铅笔盒,把她的手工制作的木铅笔盒比得那样寒怆。让她受到伤害的不只是铅笔盒,也包括闭塞的台儿沟所保留的一天只吃两顿饭的落后的生存方式。
当真实善良的香雪明白她和她的台儿沟被人耻笑的时候,她的内心也就埋下了对那个时代的现代工业文明的热烈渴望。只要能拥有这种铅笔盒,她就能理直气壮地生活在想通文明世界,失去的自尊就能找回,再也不会被人看不起。
《哦,香雪》是内心自身价值的冒险活动形式;小说的内容是由此出发去认识自己的心灵故事,这种心灵去寻找冒险活动,借助冒险活动去经受考验,借此证明自己找到了自己的全部本质。
《哦,香雪》在此意义上就是是关于香雪出发去认识自己的心灵故事与形式,
她历经冒险考验,最终找到了全新自己和自身价值,在象征意义上香雪的心灵故事也是八十年代初期中国人的心灵故事,关于出发冒险追寻考验证明认识自己。
《哦,香雪》即便描写铁轨穿越台儿沟地带的这样的近乎拟人化的叙述,还是以台儿沟这里的人的眼光和视角,以香雪凤娇等这样一群乡村少女的心理感受视角,选取了一个类似于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方式,全知叙述模式中的第三人称人物有限视角叙述描写。
小说先是内部倒叙了香雪作为台儿沟唯一的初中生,却只能用着木匠父亲为她特制的小木盒当作铅笔盒,同桌有自动铅笔盒蔑视香雪连只像样的自动铅笔盒都没有,这是鸡蛋交换铅笔盒的前因与伏笔。
小说叙述到香雪陪同女伴们来火车站点与乘客做买卖,香雪意外看到女乘客的铅笔盒她发自内心深处的渴望就变得那么真实诚挚,让读者竟也一起期盼她真的能得到换到铅笔盒。
作者运用香雪的第三人称人物有限视角叙述发生了效用,已经影响使得产生了与人物相伴生的入戏的情感心理,希望香雪能够换到这只自动铅笔盒。
读者才会在读到她最初被女学生婉拒、不开车窗的情节时替香雪着急,而读到香雪学着北京话的样子轻巧地跃上踏板,打算最快速度鸡蛋换回铅笔盒,
香雪终于站在火车上了时读者心理随着松了口气。
《哦,香雪》,火车和铅笔盒对于香雪而言同样重要,火车和铅笔盒就是文明和文化的象征了,火车冲进深山的同时也冲进香雪的内心。
台儿沟的姑娘们,每逢列车疾驶而过,她们就成帮搭伙地站在村口,翘起下巴,贪婪专注地仰望着火车。 姑娘们看火车刻意地梳妆打扮,穿上过年时才穿的新衣裳,她们对于火车仍然一往情深。
她们对于火车的陌生新鲜感、敬畏刺激性,像看情人一样看着它。
火车给她们带来了梦想、希冀和对远方的无穷想象,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构想的开始起点。
姑娘们在这一分钟里开启了美好的现代生活,和美妙的现代性体验,她们看到发现了许多新奇的洋气的现代的人和物。
铁路和火车的到来,使姑娘们进入商品生产和流通体系当中,参与新型经济关系中来。
车站火车停留一分钟时刻,农产品工业品二者不等值不等价买卖成交,全靠双方心中良心衡量。
她们手中的农产品变成交易对象即成为商品,实现交换价值,走出大山,走向四面八方,成为消费品,现代经济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
《哦,香雪》产品的流动交换构成了交易活动,正是有了这个自发市场的存在,使姑娘们遭遇了新的生命境遇,促使她们成为新的社会关系和经济结构中的现代主体。
小说描绘了八十年代初的社会变革给山村少女精神世界带来的变化,她们生命意识的觉醒,以及她们逐梦的执着与艰辛。
小说更深刻的意义,在于借助台儿沟的一角,写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从历史的阴影下走出,摆脱封闭愚昧和落后,走向开放文明与进步的痛苦与喜悦。
小说的婉丽清新和纯净优美这样的叙述基调,采用的台儿沟姑娘的视角,与读者积习已久所形成的城市人的视角,构成一种视角偏差,才会愈加显示出所写一些物事和细节的生动有趣和别具特色。
小说也能小有微澜,略有悬念,正是作者所采用的第三人称人物有限视角叙述,才让本文的小说叙事有着动人的叙事效果,叙述变得生动和别有意趣。
文章构思精巧,语言精美,描写细腻,以纯净的诗情,隽永的意境,淡雅中饱含诗情,大自然的一切均被赋予了生命和灵性,完成了对生命和生活的礼赞,树立了新时期文学一个独特的美学典范。
文章叙事结构疏密有致,已经在不经意间让读者随着小说的情境和人物,去期盼下次的火车经过和下次她们与列车员小伙子的重逢。
作者没有秉持世故的城市人的视角来看待故事的人与事,是以清新婉丽的笔调,将小小的生活场景诗化,创造了空灵,蕴藉的艺术境界,又在这纯净的境界中寄寓了严峻的思考::那淳朴淡远的美好迷人的,令人不由自主地去欣赏赞美,又是与贫穷联系在一起。
小说结尾讲到,是以来寻找香雪的姑娘们和呐喊收束全篇:哦,香雪!香雪!
《哦,香雪》是新文学史上极具历史文化意识的乡土文学作品,作者坚守着诗意化的美学理想,使得他对其笔下的乡土中国的某些区域一方面深情地眷恋和颂咏,歌唱闭塞贫瘠落后的环境中的生命灵性,赞扬洋溢在其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
《哦,香雪》没有离奇曲折的情节,没有刻意设计情节和矛盾冲突加强故事性,人们又容易忽视它的精彩,甚至对其中的人物产生误解,主人公香雪很多美好的品质也不难发现她同样具有虚荣心,几个山村少女可爱的形象却鲜活地展现在细心的读者的眼前,这大概是作品能获大奖的重要原因。
《哦,香雪》,本书收录了短篇中篇精品文章,是铁凝创作的短篇小说,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青年文学创作奖,初刊于《青年文学》1982年9月号,次年被《小说选刊》和《小说月报》转载,《人民日报》破例在1983年3月连续两日刊载节选,先后被翻译成英法意德等多语种文字出版。
《哦,香雪》被收入人教统编高级中学语文课本高中阶段,入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列入《教材中心全国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入选中国艺术研究院照耀下百部文艺作品榜单。
《哦,香雪》曾被改编成连环画,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同名电影, 获得了第4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儿童片水晶熊大奖。
铁凝,女,汉族,1957年9月生,河北赵县人,1975年7月参加工作,197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高中学历,文学创作一级。现任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共6000字)
2025年03月19日19:19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