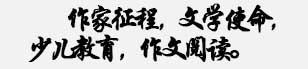耕种志(散文作品)
青年作家:马森铠(曲靖人)
(一)
以土为舟,犁锄为桨的人,耕种,是他们飘摇的终点,航程的岸头。土,耕而为田,在耕种里,人们打理出一把把名为野草的乡愁,有时,秋风把它吹成一座座坟,围绕着它们的,是一片片哨兵般的玉米、红豆、烤烟。
青山围住平原,碗状,称为坝子。碗底,平,肥沃的田园是人们最好的耕种的地方。粮在碗,人们耕种的意义也生动了几分。耕,大多是父亲的事。父亲的木犁早已换成了一架铁犁。换的意思是取代,从木犁上取下的犁头和犁耳,套在了铁犁上。被取代的木犁,只能作为烧火的柴木,随之消失的,是木犁犁至坚硬处,挣扎的咯吱声。种,是母亲在父亲犁出的犁沟里,播下种子。少数时候,我成为施肥者,一场耕种的作业中,三人行。
高原之上的耕地,在山,在谷,在坝子之中。聚居在山区的村庄,耕地也大多在山上。山地多石,山区村民的耕种,只能以木犁或者是铁犁为主。
街上卖木犁的人,是隔壁村的木匠,也是十里八乡中唯一的犁匠,姓王,人们叫他王师。在家乡方言中,师字,人们念si音。被称为师的人,乡间少有。王师的犁,犁身轻,木料却坚硬如铁,打足两把,遇街则卖,根本不必苦守。我和父亲曾在天还未明时就上街等待,买犁的人,还在陆续赶来。等待的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目光中却总是藏着锋利的一瞥——那是王师上街的方向。我和父亲并没有买到犁。邻村的刘拐买到一把,是因为王师到时,刘拐以一种让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和姿势扑上去。他死死的抱着犁,像抱着生命里最后一根稻草。卖完犁的王师,也并不急于回去,他在人来人往的石阶上,将日子抽得悠闲。买的人多,许多村民都是自备木料,上门求犁。和大多数消逝的珍贵事物一样,自从钢材盛行起来,王师就从街面上消失了,后听说他在贫寒中病亡。由此,使用木犁的人,就很少见到了。
铁犁,不过是以铁之骨,重塑了木犁之身,扛在肩上,肩头更沉重了几分。使用木犁或是铁犁,仍然是一手扶犁,一手拿鞭。挥舞鞭子的破风声,是对牛最好的约束。村为邻,田地相接,刘拐的田在父亲田地的东头,只有他还在用木犁耕种。我第一次扶犁,扶的便是刘拐的木犁。犁虽轻,我的身高却没有达到能够自信俯视木犁的高度,双手紧握扶手,牛走,犁浮出地面。不出意料的,犁倒在地上,牛拖着犁,犁拖着我,泥土的滋味略显苦涩。大伯喜开玩笑,我学犁时,他在旁边。犁至坚硬处,牛拉长身子,他告诉我,牛拉不动犁了,你要在后边推着。我推着犁,犁吃土越深,牛越无法拉动,自此沦为笑话。第一次扶犁,迄今为止,也是我的最后一次扶犁。从以耕种为生的家庭里出来的我,没有学会耕种的本领,自觉羞愧。
微耕机,像春风暗换人间。我惊讶于我竟毫无察觉,仿佛某个清晨醒来,整树整树的,就都是盛夏了——田地里,人们都使用着微耕机耕田。铁犁的牢固换不来耕种的速度。改变耕种速度的,是微耕机,人们称为铁牛。父亲的铁犁换成了微耕机。刘拐只有一条腿,他无法使用微耕机耕种。往日里两家都要干一天的活计,父亲在上午就早早的收工了。忙耕的季节,微耕机没日没夜的在地里叫嚣。微耕机耕出的地,土壤更为细致,田地更为平整。木犁或铁犁耕出的地,人们往往要耙上一遍,但如今,耙齿上早已长满了锈迹。每年耕种的时节,大型耕地机同样会来到村庄,平坦宽阔的田地,人们大多选择使用大型耕地机耕种,木犁或铁犁在山地地形的耕种中,很难被取代,坡度较大的田地,微耕机同样也无法耕种。
也许世上的事物,无论新旧都各有用处吧,这就像车水马龙的城市,有热闹喧腾的一套精英法则,而粗沥静寂的乡村,也有世人难以想象的真实存在感和淳朴的快乐。
(二)
家乡的耕种分为两季,一季大春,以种玉米和栽烤烟为主;一季小春,以种油菜和麦子为主。
耕种的人,以节令为信条。大春的耕种在四五月份。玉米是家中每年必会种植的作物。玉米对乡亲们而言,有三宝:玉米粒、秸秆和玉米芯。乡亲们会在自家后院圈养一群土鸡,在厕所旁搭上猪圈,放上一口石头凿出的槽,玉米面和鲜嫩的野菜煮出来的浆糊,就是猪和鸡的吃食了。不过,上好的玉米,自然是要拖到街上去卖的,一些富裕的街镇人家没有种地,粮食蔬菜都要上街去买,他们也是我们的主要的顾客,虽说赚了他们的钱,但父母私下里是瞧不起他们的,因为连蔬菜,葱蒜都不种的人,实在可以说是懒散,关键是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城市人,也敢这样糟蹋日子?玉米秸秆是牛过冬时必不可少的食物。冬天,百草尽枯,牛食玉米秸秆直至来年春草回生。在一定程度上,上一年耕种的作物,会成为下一年耕种的准备。以猪粪发酵、腐化过后的玉米秸秆,成为下一年耕种时松软肥沃的养料。物尽其用,耕种与生活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样在一些细微末节处体现出来,玉米芯就常被人们做烧火之用。近年来,有人远道来到村庄,向村民们收购玉米芯,以前并不值钱的东西,在人们眼里,又珍贵起来。
四五月份的耕种,尤以烤烟,最难成活。栽种烤烟时正值天气最为干旱的时节,天空给人以持续的晴朗。一两朵云,以蔚蓝的天空为底色,变幻的美,给人以绝望。烤烟需先育苗,再移栽到土里。在温室中培育出来的烟苗,根茎柔弱细小,成活率低。新出温室的烟苗像一条被丢进沙漠中的鱼。它迅速的失掉水分,栽种的过程更像是一个抢救的过程。春雨贵如油,人们渴望下雨,但高原之上的雨,来的迟。栽烟,需要大量的引水灌溉。烤烟的种植,虽过程繁琐,但收入,却关乎人们的命脉。指着烤烟过日子的人们,顶着四五月份的烈阳、六七月份的风雨,顶不住的,是一场说来就来的冰雹。风雨难测,冰雹对烤烟的打击极具穿透力,以至于人们过于轻松的就能感受到尖锐的疼。
小春的耕种在九月和十月之间,相比烤烟而言,小春的耕种要简单许多。大春收割之后便可直接撒种耕土。不过,由于连年的耕种会导致土壤肥力降低,部分乡亲选择耕而不种,让田地休养生息,多半是在严寒的冬季,昆虫,杂草和田地都进入了深度睡眠,经过一冬的休息,来年春风一吹,山野田间生机焕发,完全热闹喧腾起来,作物在天地间呈现它的坚韧不拔。
在耕种之前,人们往往花大量的时间筹备肥料。“人欺地皮,地欺肚皮。”这句话常常成为人们带着悔恨的感叹。人对庄稼苛扣肥料,那么庄稼定会苛扣人的口粮。冬春之季,年关前后,多有村民上山铲草皮,我和父亲也不例外。山中少有人迹,植被茂盛,一岁一荣枯,大量的落叶枯木堆积出厚厚的黑土层,肥力充足。铲草皮,就是为了铲起这层饱含肥力的土壤。运到家中的草皮,与畜粪、秸秆合沤,成为人们耕种时上好的肥料。近年来,人们多选化学肥料耕种,而农家肥用者渐少。人们不再上山铲草皮,只剩空荡荡的树林,守着空荡荡的斜阳。
古言有训,三分耕种,七分管理。耕种之后,还需除草除虫。除草,以锄,以镰;除虫,以左手,以右手。左手上的疤痕是小时候参加除草最为深刻的见证。玉米长至脚踝的高度,一年的除草便开始了。练习使用锄头的岁月里,不知道牺牲了多少无辜的玉米作为代价。除草过后,等玉米长至膝盖的高度,人们开始培土。培土是为了防止玉米倒伏,但培土的过程也是玉米第二次除草的过程。农药,是人们管理庄稼的一个巨大的跳板。农药出现之后,人们也不再使用锄头除草。有的农药可以帮助玉米生长根茎,人们也不必再培土。
使用农药之前,作物多采用混种和套种的模式。母亲会在玉米地里种瓜、红豆和瓜子等作物,这类作物种的数量少,一般都只是自给自足。但混种的作物打药极为不便,玉米除草剂会杀死除玉米之外的任何杂草和作物。家乡的地里再没有种植瓜子。瓜,被种植在田地的四周,沿田埂攀爬生长。而豆子矮小,则可以与烤烟套种。
高原山多地少,耕田,挤在青山之间。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使人们耕种的时间大大减少。而余下的时间,人们也并不愿在闲暇中度过。许多村民在完成一年的耕种任务之后,就成了附近厂区的一名零工。耕种与打工,两不相误。耕地少,许多村民也不愿留在家中,他们把土地租赁出去,另谋生路。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村民都会选择租赁,一些村民在自己的田地里栽种下有经济价值的树木,成材之后,便可卖出。
高原的耕地以旱地为主,水田较少。水田多分布在沟谷低洼处,以阶梯的形式展开。家乡的水田一年耕种一次,栽种水稻。没有抽水机之前,人们遇雨而耕。家乡稻谷的收割在十月份,收割之后的稻田,成为闲田,土壤容易板结。在雨季来临之前,人们会把稻田翻耕多次,使土质松软,土粒变小。山雨来时,山间水起,人们挖沟引水泡田。水田的耕种受水源的牵制极大,而可以耕种的水田面积却少,一些人家都已放弃了水田的耕种,荒草连年疯长。相反,许多人家则是将水田改成旱地,种植旱地作物。
黄土安身,耕种则可以立命。耕种的地方,乡愁如黄土。
(三)
以耕种为生的人,分不清自己耕种半生的,是如命运般挣扎的黄土,还是如黄土般坚硬的命运。用一条腿耕种的,我仅见过刘拐一人。刘拐,或者叫跛脚,村里人都这么叫他。这类形容他身体缺陷的名字,代替了他的真名,存活于世。他的真名叫什么,不重要了,那个名字,只藏在自己心里,像一枚埋在黄土深处的铜板,再发现时,已改换了朝代,锈迹斑斑。有时候自己在心里叫自己几声,自己没有答应。他叫的人,已然死去。
在戛者的山坡上,一棵松树横向生长,刘拐倚着它,将烟头的日子,抽得变苦发黄。刘拐栽烟,同样抽烟,栽烟是为了活着,而抽烟,则是为了找到一些看似没有意义的意义。在抽烟的时辰里,他回忆着记忆之外的日子。他回忆的日子,不过是把记忆里另一些集市上的水果摊、米线店、拔牙桌……搬进他想回忆的日子里,使一个本就没有记忆的日子,从真实的无,变为虚假的有。我们上山放牛时,他已经睡去,我们偷偷从他身边拿过水烟筒,用剧烈的咳嗽唤醒他轻薄的睡眠。然后,他咧开嘴笑,黄玉米般的牙齿,像乱石一般,铺陈出山顶崎岖的峰线。他的头发是他一个人的乱世,在里面,藏有战争和灾难,藏有数不清的腐朽与凋零。
他说他的腿,是在一个赶集的日子里没有的。母亲的背,成为了一个温暖的陷阱。他在母亲的背上,哭喊声中,有十二月的雪花落下来,雪花碰撞着雪花,美在破碎。四十年前的街道,和现在同样拥挤,最后一班客车,人们挤进车厢,将暮色,挤出车外。上车的地点,没有变过,只是水冬瓜树长得粗壮了,人们削去了他的头部。他在母亲的背上,跟人们一起挤,他在母亲的背上,说不清最后一个上车的,是母亲还是他。说他们上去了,或者是没有上去,这样的说法,都带有不准确性。他的一条腿留在了门外,他的一条腿在门外的暮色中,暮色染红了半边天。他还没有学会走路。不平坦的路上,车子摇晃着一群人本就不稳定的命运。
他说的时候,照常抽着烟,照常咧开嘴来笑。他的腿变得血肉模糊,在车门缝里,被拉长,像煮熟的面条,像春风吹过之后的柳条,失掉筋骨,失掉力量,失掉被称为一条腿的价值。常年抽烟,他的食指还有他嘴唇旁呈圆形的一圈,被熏得焦黄发黑。尽管他的皮肤,本来就是一片贫瘠的土地。
他的一只手和一根木棍,共同的组成了他残缺的另一条腿。他十五岁学习耕种,如今就要年过半百。他说他耕种的土地,跟别人一样肥沃,他收获的庄稼,跟别人一样饱满。我们面前的麦子,被风吹弯闪出一刹那的白,又直起身子,显示出深沉的黄。这是他的麦子,像一片武士般立在山头,以麦芒锋利的刀对抗饥饿的戟。
有时我们上山放牛,他正在犁地。他失去的是右腿,在犁地时,他用木拐和右手支撑起他的身子,左脚向前摆动,很吃力的,跟着老牛行走的速度。左手扶梨,单手控制着犁地的深浅。他的手中,缺少一根鞭子。犁田时,他常常摔倒,他摔倒时,竟比他站着,更像一个人的模样。我们像欣赏一幅从未见过的风景画般,看着他,吆喝着牛,从田的这头,到田的那头。我们就这样看着,他就那样犁着,仿佛他在犁一片亘古的荒漠,我们的目光,犁过他犁过的每一片土地。
母亲不同意锯掉他稀碎的右腿。她让医生从自己的身体上,取出肉,取出皮,组装成他的右腿。母亲是喝农药死的,说到这里时,刘拐指了指旁边的土堆,没有墓碑,野草在上面疯长,一个不像坟墓的坟墓,一个只像土堆的土堆。
他说拆线之后的右腿,满是疤痕,他怀念那条满是疤痕的右腿。他的腿终究还是跟他的身体一样,学着生长。十五岁,学耕种。十六岁,在耙田时,他掉进了耙里,耙齿钩住他的右腿。母亲赋予他右腿之上的血肉,在满是土块的田中被长久的拖行,一点点消失。他的腿开始萎缩,医者无力。母亲是在他的腿开始萎缩之后才喝的农药。嘴里吐着血,浓得发黑的血。这是别人告诉他的,别人像他跟我们一样,讲故事给他听。在故事里,只有主角是他,连故事都是别人的。萎缩的腿,像秋风吹着一棵死去的树,慢慢变干。慢慢的,就只是一些死去的皮,包裹着一些死去的骨头。死去的皮和死去的骨头共同组成了他身体里死去的一部分。他的腿还是锯掉了。每年冬天,他跟父亲拉扯着锯子,在院子里准备过冬的柴木,他会看到,那是他躺在木马上,父亲和另一个自己,在锯着自己的右腿。一堆柴木,那么多的圆形的疤痕,每一个都像是他的。他把裤腿解开让我们看他的疤痕,圆圆的形状,像一枚冬日里干瘪的果实,像一轮失魂落魄的落日。
“三十八岁那年。”是刘拐说到一半的一句话,说到一半就停住了,像雨停在空中。又说年纪对他已经没有了意义。年复一年,刘拐每一年都只是在耕种,耕种同一片土地,耕种同一种粮食,像雨从空中落下,从头到尾都是雨,没有改变。父亲带回来一个女人时,他才知道,他已经三十八岁了。他不知道他的生命里会出现一个女人。女人在父亲的身后,出现在他的眼前。他看着这个女人,看着这个站在门框里的女人,她进来时,他第一次看到了家里老旧的阁楼打开了一扇门。彷佛三十多年来,这扇门像一堵墙的存在,仿佛他从来就没有打开过任何一扇的门。门这个字眼,第一次出现在了他的生命里,还有一个女人。
其实女人才是他的门,女人出现了,门才出现,女人没有出现之前,世界上还没有过门。他看着那个女人,她的胸前挂两轮圆月,挂两个无数男人渴望团圆的中秋节。从此,女人成为他生命里的另一块土地,他耕种着这块土地,播撒种子。
女人的智力是有障碍的,在她的世界里,一不是一,一可以是任何数,一百元的钞票可以只是一棵白菜。女人来到之后的日子,是欢愉的。刘拐的女人总是咧开嘴笑,吃饭时,饭在嘴中,仍然笑。女人的笑是笑世间一切事物的笑,无关悲喜,无关生死。但刘拐接受这个女人,因为,她是门,她是刘拐的门。刘拐去田里做活计的时候,便给他的牛套上车,拉着他,也拉着他笑着的女人。
村里热闹的时候,不只有办喜事的时候,办丧事的时候同样热闹。热闹是一群人聚在一起,跟办什么事,没有多大的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村便是一个家族,家族或大或小,或者是,一个村就是一个家族的分支,有同样的姓。外地搬来者,在少数。刘拐所在的村庄便是刘姓为主的一个大村庄。村里大事同办,小事各忙已是约定俗成的规矩。刘拐恐惧这样的时刻,在耕种里,他是故事的主角,而当所有的主角聚在一起时,他又远在舞台的千里之外了,他帮不上什么忙,或者说,他无法帮忙。他,只是他一个人的主角。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他才是他,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是刘拐,是跛脚。
他希望日子像一潭死水,不要有风,有风的时候会惊起波澜。长年拄拐杖,他的身子渐渐的弯了下去,像一张弓,像一根做弓的木料,以他不该弯折的面,弯折下去。他放牛时,将牛的鼻绳和他的手绑起来。牛吃庄稼时,他就拉动手中的绳子。绳子,将他的命运和一头牛的命运绑了起来,其实有没有绳子,他和牛的命运也是分不开的。上山放牛的时候,他会和我们选择同一个山坡,牛看见牛,狂奔而去,牛也害怕孤单。他像牛看见牛一样,高高低低的向我们走来。他害怕很多的人,同时又害怕一个人。仿佛人少的时候,别人对他的嘲讽就不再是嘲讽,仿佛在这样的时刻,少量的嘲讽可以忽略不计。
刘拐父亲的死,是波澜不惊的死。他说他父亲的死像是他买好车票,上了列车之后,自然而然就到达的一个地方。刘拐说他父亲死的时候,脸上像一碗兑水之后的中药,竟然化开了几分。那样的脸,我只见过一次,像柿子从容的挂在秋天的树上。他的从容里透着我的惊恐,一种难以言表的惊恐。他说完他父亲的死,又开始说他父亲给他带来了一个女人。他指了指远处,他说他父亲的坟在远处的山上。他艰难的站起来,手遮挡着眼睛,再把眼睛眯成一条缝。我们顺着他望的方向望过去,一整座山映入眼帘,一整座山,都像是坟。
刘拐的家,在山上,在他耕种的田地旁边。几根简易的木头支撑起一个狭小的空间,一张塑料防水布盖在上边,破烂的部分被风吹着,像一面立在高处的旗帜。他说这是他的家,但我们都知道那是他父亲为他搭建的简易避雨棚。他说这是他的家,我们也信。他待在这个简易棚边的时光,远要比待在村子里的瓦房下的时光,多出很多。
刘拐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上山来,我们放牛,便只是放牛。他在田的东头再分出一小块地来,种土豆,种够他一个人吃一年的土豆。土豆成熟以后,挖出来,埋到简易棚干燥的泥土下边。他不来的时候,我们照样拿他的土豆烤。刘拐的女人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健康的儿子。再见到刘拐,日子已经过去一月有余。刘拐的脸上每天办起了喜事,他的脸,仍然像一张老旧的木桌,只是,如今的木桌上,摆上了一件难得的光鲜亮丽的瓷器。他说他的儿子像他耕种的最肥沃的土地,有人调侃说,是他耕种的土地上,长出了一株肥壮的庄稼。他的儿子,像是他三十多年的耕种,第一次有了收获。刘拐走进他的雨棚里,拿出土豆来烤,他走路的样子,像是比以前利落了几分。
戛者村,刘拐所在的村庄。入村口,右手边一片水冬瓜树林,左手边一片竹林,车子从中间穿过,转过弯,村庄便出现在眼前了。村庄临水而展,湖水弯曲的地方,村庄也附和着它弯曲的幅度。刘拐家在村庄的深处,土墙围成的院子,没有门。三间矮小的猪圈,两间养猪,一间堆放着过冬的柴木。土墙之上,裂痕划破屋中的生活,蜜蜂在墙上打满密密麻麻的巢穴。矮墙上,挂着刘拐一生对抗命运的武器: 镰刀、锄头。一整面墙上,过多的留白,这些本来空缺的部分,多了些大雾般的茫然。那是刘拐走后的日子,一座本就没有多少生气的屋子,变得更加死气沉沉。那几年,打工的潮水席卷了村庄,刘拐是跳入潮水中,又被拍打回岸上的唯一一个。刘拐被拍打了无数次,是父亲给他的土地留住了他。父亲给了他两块土地,第一块土地养活了他的肉体,第二块土地是他的女人,养活了他的精神。他说他并不是想出去打工,他想到了死。刘拐想死在外边,死在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异乡,他怕他死在家乡之后,人们在他的石碑上将他的名字刻成刘拐,那样的话,他一生的耻辱将会永垂不朽。他竟然没想到人们会不会帮他立一块石碑的问题。好在他有了女人,父亲给他带回来了一个女人,他不再想出去,他回到屋檐下的矮凳上,打磨着新一年耕种要用到的农具。
日子继续耕种下去,耕种与收获在轮回。风一阵阵的吹黄麦子,黄土的脚镣又成为他无冕的皇冠。那么多的麦子,每一株都是他梦境的一部分,每一株都以饱满,制造着他的天堂。在他的天堂里,他的女人在笑;他的儿子在奔跑;他的老牛在他的牛车旁嚼着他的麦草,新割的,一大捆,带麦粒的麦草,这是他奖赏给他的老牛的,老牛正嚼得起劲。割麦子时的刘拐,是跪在地上割的。草编织而成的凳子,成为他割麦时的右腿。多数时候,他需要跪着,跪着收割,跪着除草,跪着生,跪着活到死亡的那一天。
他在天堂里收割,地狱的消息从人间传来。他的儿子掉进了一口荒废的井中。儿子口渴,但并没有从女人那里得到水,便自己找了出去。捞上来时嘴唇已经发紫。那是刘拐用一条腿跑得最快的一次,这一次,他没用拐杖。人们说他跑过去的时候,上天给了他一条右腿。他死去的儿子在他的怀中,他活着的女人在旁边,在血红的晚霞之下,哈哈大笑。那个笑的无比灿烂的女人,是死去的孩子的母亲。
几个月后,刘拐养起了山羊,一只公羊,一只母羊,母羊已经怀了崽子。山羊的身上,有刺鼻的膻味,牛多不喜欢。山羊靠近水牛时,牛会喷着鼻子,摇动着弯曲而锋利的角,驱赶山羊。放羊的羊倌告诉刘拐,山羊和水牛要分开来养,水牛弯曲而锋利的角随时会穿透羊的身体。刘拐点了点头,沉默之后,又点了点。他将山羊和水牛分开来,但又让山羊和水牛保持在一定距离,水牛能闻见山羊刺鼻的膻味,山羊在水牛牛角摆动的范围之外。在上山放牧的路上,他牵着牛,女人牵着山羊。牛喷了喷鼻子之后,卯足了劲,顶向了山羊。对于牛宣誓主权的举动,山羊早已保持了充分的警惕,两只山羊几乎同时以灵巧的身姿躲开。没有躲开的,是他的女人。顶向山羊的角,坚硬,贯穿了女人的身体。刘拐还是刘拐。一条腿的刘拐,他发疯般地扑到女人的身上,无声的哽咽像石头顶在喉咙处,渐已冷却的血,将痛苦和乌黑的死永远缠到了他的旧衣上。
刘拐失掉了他的收获,又失掉了他耕种的土地。失掉了土地和收获的人,不再是耕种的人。他在一片土地上,耕种了自己的前半生,后半生,是另一块土地在耕种他。他全部的身体,都接近他手中的木拐。木拐,从来都不是他的名词,木拐,一直是他的形容词。刘拐,也不是他的名字,只是他的形容词。
他耕种的土地上,野草重新缝合。三座土丘,一座偏小,两座立有碑。其中一座墓碑上,竖着刻有四个字:刘拐之墓。
云,是空中的山,而山,是地上的云,都在深处,藏着老旧的阁楼和新埋的坟。
云,造着浮世的象。在云朵之下,戛者最高的山上,刘拐的一生,长眠于此。
高原之上,一群耕种的人,挖开泥土,就注定是地心中的一颗种子。他打理了一生的野草,在每一年的山火过后,又重新盛开在坟墓之上,重新盛放在许多许多个春天里。
(完)
作者简介
马森恺,云南曲靖人,曾就读于文山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有诗歌发表于《边疆文学》《滇池》《零度诗刊》等刊。 马森恺凭借散文《耕种志》获得“第八届全国大学生野草文学奖散文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