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甸寻蜂(散文作品)
文山作家:陈刚(昆明寻甸汉族)
言及野蜂,人们联想到的,多是其纤薄的羽翅,灵巧的身姿,勤劳、自由的代表;或是其尾部细长的毒针,坚利的双颚,以及被螫后的痛感。定义,是人对于事物认知方式的一种。就野蜂而言,除却上述的,应还有不少贴切的言语可用。然介乎两者间,被遗漏的部分又该怎样定义呢?许多时候,随着人理解的深入,认知发生矛盾是在所难免的。我曾经喜欢臧否人物,但由于自身认知的浅陋与经验的不足,难免有失偏颇,贻笑大方。如同人初次在山间寻蜂,入林时的踌躇满志、成竹在胸,往往只会加重求而不得的沮丧感。
云南地处高原,山区草木繁茂,多奇珍与异草。我曾听过这样一则关于云南穷困的戏言:云南人早上吃松茸,中饭吃蜂蛹,下午吃牛干巴,吃腻了就抓羊杀,不穷才见鬼了。虽然戏言,却也可看出云南的特色吃食是不少的。其中提到的蜂蛹,在云南是一道难得的美味。难得的原因有二:其一,雄蜂为一年生昆虫,蜂群内仅有一只蜂王,繁衍速度较慢,蜂脾只在农历的七八月份最大,最饱满(唯有黄长脚蜂与蜜蜂为多年生蜂群。)再者,野蜂巢筑在隐秘的树梢、枝杈间,枝叶掩映的,人难以寻觅。
味美之物,百闻不如一品。蜂蛹是山民重要的蛋白质来源之一,山区的农人寻到野蜂巢,多是自家烹制后消受。故而,虽物以稀为贵,却鲜有带至集市贩卖的,常出现价高物少的现象。
蜂六足,触角、羽翅和跗节呈橘黄色;躯干乌黑发亮,有条纹和成对的斑点;腹藏毒针,全身长有细小的绒毛。蜂按体型由大至小排列,常见的有:中国大胡蜂、黑尾胡蜂、黄腰胡蜂、小黄蜂、黄脚胡蜂、黑蜂、黑盾胡蜂、黄长脚蜂和蜜蜂。这大致构成了蜂的群像。野蜂少见,识蜂者亦不常有。蜂的外观大同小异,加之隐于山野,了解其隐秘的差别的,终归是少数人。
在我的故乡寻甸,人们寻到的野蜂,皆可烹食。然烹制的技艺用于蜜蜂身是使不得的,烹食蜜蜂虽不犯法,却为人所鄙。
蜜蜂蜂群内,多是工蜂。工蜂自破蛹后,便四处飞舞,采集山间的百花花粉,酿制蜂蜜。如若一只工蜂寻到蜜源,便会在巢穴门口“跳舞”。工蜂跳圆圈舞,表示蜜源离巢近;跳“8”字舞,表示蜜源离巢远。工蜂跳舞时,头朝上,表示蜜源在阳坡;反之,则表示蜜源在阴坡。另外,工蜂舞跳的快慢,也包含着蜜源源近的信息——快近、远慢。
蜜蜂的尾刺与其它蜂群不同,御敌时,为将毒汁充分注入侵犯者的体内,进化出了形似野树莓的倒刺。蜜蜂尾刺宛若一根针头,使用过后只能“废弃”,尾刺上的倒刺会将其毒腺连同脏器扯出。不多时,蜇人的蜜蜂便死了。所谓“蜂死剑活”,蜜蜂的毒腺在脱离躯体内后,仍会挤动注射毒汁,对肌体造成伤害。
对于登上顶峰,亦或尚处谷底的人与事物,从来不乏吹灭毛求疵,欲将其击倒者。工蜂的一生目标明晰,只做五件事:筑巢,采花粉,酿蜜,喂养幼蜂,清洁巢穴。工蜂受蜂王的驱使,奔忙一生,御敌即死。或许有人会觉得这样活法过于苟且,不及巢内黑色臃肿的雄蜂那般安适。
作为低等生物,工蜂在其不足一月(约二十八天左右)的时间里,用毫不懈怠的专注力做好了这五件事,我想它们是值得人青眼相顾的。
我在老家读四年级,立夏前后,外公家院外传来“嗡嗡、嗡嗡”的响动。祖孙二人出门一看,院里遮天蔽日地飞舞着正在寻觅巢穴的蜜蜂。外公见状,急忙到菜园里取来土,左手提着一桶泥,右手对准蜜蜂飞行的方向抛洒,嘴喊“蜂落、蜂落”的咒语。紧凑的咒语和松散的土,很快扰乱了蜜蜂的飞行。不知去向的蜜蜂,只得先落在院儿里的鸡嗉子果树上。蜂群汇集的速度极快,不一会儿便聚成了兰花碗大的一窝。
鸡嗉子果树的叶片正在生长,油亮亮的,随风摆动,院子暂时静了。
山里的东西,除却公用的,谁先发现的便为谁所有。毫无疑问,这窝蜜蜂是我外公的了。外公不会收蜂,请了村里的养蜂好手开升前来帮忙。开升人长得精瘦,除了蜂养的顶好,爬树的本事在村内也是一流的。
开升不吸烟。喝过茶,他戴上棕树皮缝制的头套,手提竹篾编成的收蜂篓,走到树下脱掉鞋子,脚掌在树干上找到合适的发力点后便开始往上爬,动作迅捷,宛若松鼠。(长期务农的人,脚掌上多少都生有硬实的肉茧子,踩在树皮上感觉痒,不疼。)爬到与蜂群齐高的位置,开升将蜂篓搁在树杆上,折取一截鸡嗉子果树的枝叶向上驱赶蜂群,嘴里念着:“蜂上,蜂上。”的咒语。蜜蜂似能听懂人语,争先恐后地爬进了收蜂篓。
直至年岁渐长,我方才得知蜂篓内涂有少量蜂蜜!飞行许久地蜜蜂哪能禁得住这般“威逼利诱”呢。
而今土坯房很少见了。幼时,在农村,若是见到谁家的土坯房上有个方形的洞,那这户人家一定是养过蜜蜂的。收回蜜蜂,外公凿了一个方洞。土洞凿的向阳,紧邻烟囱,温暖干燥。开升将蜜蜂引至蜂窝,闲坐着饮完一杯茶,便回家去了。外公依据土洞的大小,为蜂群制作了一块松木门。木门开有二指宽的小孔,供蜂群进出与透气。
因地制宜地进行废物利用,是人对生活的让步与尊重。牛虽有四个胃,草料经过消化,反刍,再消化,其排泄出的牛粪中仍有大量有的机质,且粘性极好。内蒙地区的牧民有收集湿润的牛粪,晒干后作为燃料使用的习惯。云南多柴火,没有将牛粪作为燃料的必要。可为能有一个好收成,耕种时除使用化肥外,还会追施些农家肥。故而也有捡牛粪堆肥的农人。农村捡牛粪者,多是年老体衰、无力下田的人,闲暇时光无事可做,便手持簸箕,沿路寻找。倘若见到此种现象,是不足为奇的。
安置上木门,土洞仍有缝隙。外公取来放牧时捡的牛粪,灶台下的草木灰,戴着橡皮手套掺水搅拌,过程宛若揉面。揉至青灰色,表示着牛粪与草木灰已充分融合,具备了类似混凝土的功效。草木灰的吸附功效,除去了牛粪的异味。用之封堵空隙,契合了蜜蜂喜爱洁净的天性。糊至木门上开好的小孔,外公特意用清水将其磨滑,以减少蜜蜂采集花粉归巢时,蜂脚上携带的花粉的磨耗。
外公是民办的退休教师,耕有少量土地。闲暇之余,他便坐在小院里喝茶,观察蜜蜂的进出。某日中午,院里飞来一只虎头蜂,直奔墙上的蜜蜂窝而去。蜜蜂中把守洞门的哨兵,见此情景,连忙爬进蜂窝内通报敌袭,蜂门内立即爬出大量工蜂。面对体型数倍于己的虎头蜂,蜜蜂站得紧凑,动作齐整地震颤翅膀,响声急促。
人最需要战胜的,多是自己内心的恐惧。马蜂打惯了秋风,深谙此理,单枪匹马地频频对蜂群发起冲击。蜜蜂的数量虽千百倍于敌,却被吓得连连躲闪。正在蜜蜂节节败退,马蜂寻到破绽就欲得手之时,外公挥动木棍击中马蜂,结束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斗争。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抗争是徒劳的。马蜂躺在地上挣扎,不甘,却又显无力。经历此事,外公对蜜蜂更加上心了,生怕马蜂再来。
据我的经验,蜂蜜最佳者,应是在石块、土层中筑巢的蜂群生产的。农历的六月,外公找来开升清扫蜂巢。开升戴好护具,揭开遮挡蜂窝的木板,用刷把清扫死去的蜜蜂,以及不知名的残留物。
刷把是苋菜接穗部分的枝干制成的。苋菜在云南也称称作小米菜,抗性强,喜热,耐湿,易生长。幼嫩的苋菜采择后可炒食,宜煮汤。苋菜汤色泽淡红,茎脆叶滑,味鲜美。汪曾祺先生在关于昆明的文章中写到过,认为田地里留下的几株接穗的苋菜,是纯乎观赏的。接穗的苋菜固美,农人留它,还有制作刷把的用途。
清扫好蜂台,开升点燃自家带来的火草,薰蜂。蜜蜂被呛人的烟味熏得纷纷躲避。露出的几片蜂脾上,封着白色与嫩黄色的“盖子”。白色的“盖子”里是蜜,嫩黄色的“盖子”里为蛹。
开升用细长的尖刀,割下了一块拳头大小的白色蜂脾塞到我的嘴里,咧嘴笑了。我轻轻嚼动,甘美温良的蜜汁霎那间溢满口腔。
开升接着割下有蜜的蜂脾,吹去不肯飞去的“顽固”。外公用一只不锈钢盆取蜂脾。有蜜的蜂脾还剩最大一片时,开升不割了。我问他为什么。“得给它留点,下次才能再割,忙了一季节,全拿了多不好意思。”开升如是说。
话语间,蜂房里的蜜蜂开始在开升胸前汇聚。慌乱的开升,左右挥手驱赶蜜蜂。奈何蜂群越聚越多,钻进衣服内的蜜蜂将开升蛰得手舞足蹈。静下心,凭借多年养蜂的经验,开升很快找到了问题所在。原来他在割蜜时不慎将蜂王弄到了衣服上。工蜂循着蜂王散发的信息素寻来,面对开升这个举止粗鲁的庞然大物,叮咬之余,急的只差说“王负剑!”
开升迅速用手里的刷把将蜜蜂引至蜂巢,嘴里再次念着“蜂上、蜂上。”的咒语,蜜蜂像食草后回圈的羊群,有条不紊地爬进了蜂巢。
外公糊好蜂窝,同开升在院里喝茶,山风拂动头顶的树叶与斑驳的光影。开升喝了口茶,捋其袖子查看被蛰的部位。他因体质与常人相异,并未红肿,被蛰的地方只显出一个白点儿。见天色尚早,开升说山里还有窝野蜜蜂,邀外公一起去割蜜。外公欣然应下。我喜动,欲同去,可外公以山高路远为由回绝了。
待阳光斜照在鸡嗉子树根部的苔藓,外公才回到家。他从塑料口袋里掰了块蜂脾给我吃。蜂脾呈翠绿色,较之土墙上割下的蜂脾,色泽暗淡不少。我本打算丢弃的,奈何外公一再说好吃,只得勉力塞入嘴里。蜂蜜入口,顿时觉得蜜汁香醇、润滑,脑海中浮现出各类野花,一股暗暗的香味若隐若现,宛若波浪拍击礁石,正欲细细品味时,却悄然淡去,尔后再度浮现,似有灵性。家养的蜜蜂与山里的蜜蜂所采集的花粉、酿制工序相同。蜂蜜口感上的差异,想必在蜂巢的温与湿度,是大山的馈赠的一种。
家花没有野花香,原是登徒子遮羞的言辞,将之改为家蜜没有野蜜甘美却是实话。野蜂蜜独特的口感受人欢喜。至于追求经济利益,给蜂蜜喂糖的商贩,其为人的品质与他售卖的蜂蜜是一样顽劣的,一样容易辨别(喂糖的蜂蜜入口极甜,回味发苦)。
近年来,除蜜蜂外,寻甸养殖胡蜂的农户也逐渐增多。胡蜂养殖失败者为多数,鲜有成功养殖的。失败的缘由是不了解野蜂生长的习性。
胡蜂的形体小,同样需要像狗熊那样找个树洞休眠。
胡蜂通过蜂王散发出的信息素进行分工、合作,是一个有条不紊的群体。蜂群结构与蜜蜂相似,唯有蜂王能够产卵繁育。中秋节后,寻甸的天气转冷,蜂王的生育机能衰弱,进食减少,直至画上死亡的句号。
蜂王既薨,蜂巢内的雄峰和雌蜂不再受到信息素的压抑,开始自由地追寻交媾对象。胡蜂没有审美观念,若是有,为了族群的延续,想必是以“刚健”为标准。我常在寻甸的山间林野里寻蜂,尚未见过跛脚的,或是断翅的胡蜂交配过。野蜂交媾于树梢上、花丛中、蒿草间。雌蜂只需交媾一次,既可产出万千枚蕴藏生机的卵。交媾后,雌蜂开始忙着寻觅适宜的地点冬眠,为来年成为新的蜂王积蓄力量。雄峰则不出几日便死了。
胡蜂多是二月苏醒,三月筑巢,四月产卵,五月寻食,六月扩巢,七八月获蛹,九月至来年打春时节,进入山谷溪流间的柴缝、树洞内休憩。族群循环往复,万寿无疆!
胡蜂休眠结束在打春前后。此时寻甸的气温尚低,繁育的幼蜂不易存活。新的胡蜂王会选择在松软的土层内筑一个零时栖居的蜂巢,待气温渐高,再寻找适宜的乔木构筑蜂巢。农历的三月至五月,野蜂数量不多,蜂巢还在地下,寻蜂是困难的。
寻蜂最适宜的时节是在农历的六月份。此时的野蜂已在树上筑巢,且蜂群数量较多。寻觅起来较为方便。寻甸的下乡,夏秋季节多是栽种烤烟。六月份地里的烟叶尚在生长,还不到烤制的时间,农活少。农人除了薅草,喂养牲口,基本无事。空闲出来的时间,人们就到山里捡菌子,寻蜂。
寻蜂既能让人品味到蜂蛹的鲜美,亦可锻炼人的眼力与耐心。我曾见外乡人过寻蜂,先是找一片胡蜂常飞的地带,用木棍插上一块生肉,吸引胡蜂前来采食。寻蜂人在胡蜂采食的过程中,将事先用薄膜做好的环扣套在野蜂身上。待野蜂采食好,不知不觉间,连同薄膜信标一同带飞回蜂巢。此种寻蜂的方法高效,便捷,寻蜂人只需要看着天空中的信标跟进,便可轻易地找到蜂巢所在的位置(若是胡蜂飞行的距离过远,还有用望远镜、无人机的追踪的。
寻甸的寻蜂方式较之前者,多少显得有点愚笨。
寻甸的人寻蜂,多是三五结伴而行。一行人进入山后,先是茫无边际地找,寻到一块野蜂较多的地方,便蹲下来吸烟,谈天,待胡蜂飞走后紧紧跟随。山里林深繁密,不乏跟丢的。寻蜂人看不见胡蜂了,便在跟丢的地方蹲点,当胡蜂再度飞过时,继续跟着寻找。直至寻到蜂巢为止。
去夏回寻甸,当晚在家住下。次日,表弟便打电话给我约我去寻蜂。吃过早饭,与父亲简单交代了几句,我便出门了。刚走到大门口,父亲突然大声喊我回去,我还以为他怪我长时间在外读书,少有陪伴他们的时间,不给去。我做好了被说教的准备,回到家中却不料他给了我一只塑料口袋。“昨日刚下过雨,到山里寻蜂,顺带捡点菌子回来煮汤吧。”父亲粗糙的面庞露出笑容。地板上还有昨夜残留的雨水。阳光照着院墙上的苔藓,绿油油的。
进山的路途两旁,玉米正在抽穗,土豆开有蓝白相间的花。山风拂面,带有蒿草气息。人愈往前走,青松掩映的道路就愈窄,蝉鸣鸟叫声就愈加清脆。行至水泥路的尽头,便进山了。
同行的唯我表兄弟二人。进入山后,他便与我分散开寻蜂找菌了。我们所去的山,村里人喊作杨房箐,是附近山林中树木最繁茂的一座,也是唯一一座会出松茸的山。山林里的腐殖质,经年累月地堆积,挖下去尺余,才可见到红土。人行其上,用力过猛便会陷下去。加之光线昏暗,土腥味混含与林叶腐败的气味,使人有莫名的兴奋感。
自踏入山林的那一刻,我与世隔绝了。平日里紧张的神经得到了舒缓,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能听到是我自己有力的心跳与山涧活泼的流动声。
山林里胡蜂飞动的响声不绝于耳,可仔细一听却又不知在何方位。我好不容易辨清了响声最大的一处。寻声追,发现据我不远处的树叶在动,心里一紧。脑海中飞速地闪现出老虎咬人、熊拍胸脯的场景。前方的树枝不停地摇动,我的呼吸变得急促,手心冒出汗珠。我正欲奔跑,树枝动的方向传来了叫清脆的叫声,定睛一看,不过是几只麻雀。麻雀在枝头上灵巧地跳跃,鸣唱,似在嘲笑我方才胆小如鼠的举动。
心境平复,我继续循着马蜂响动的方向寻去。一只美人蜂映入了我的眼帘。它正在一段松软的树桩上采集木料,我提着手里不时捡到的菌子站在一旁观看。美人蜂通体金黄,躯干上有黑色的斑纹,宛若穿着一身时髦的衣饰。
美人蜂用双颚采集够木浆,绕着木桩盘旋几圈,记好位置,转了个弯便径直朝山林更深处飞去。我紧随其后寻去,步法虽快,但还是由于林叶过于繁密跟丢了。
我在跟丢的地方没头没脑地探寻着,不曾想在发现了一只肥大的松茸。我低头正欲去捡,脚旁的灌木丛里突然传出“咕”的嘶鸣声,灌木丛随之猛烈地摇晃。猝不及防间,我摔的仰面朝天,大叫一声“妈妈呀!”,塞了一嘴的落叶。
我倒下的同时,也看清楚了惊到我的野物——一只麻色的野鸡。野鸡起飞,本是不需要助跑的。惊吓到我的同时,它也被吓得忘却了本能,迈着两只刚健的鸡脚奋力遁去了。
野鸡为何离我这么近,为何遁去?我站起来摸不着头脑。低头拍打身上的泥垢时,我发现身旁的灌木丛内有一个树叶堆积的窝,窝里已有三枚小蛋。蛋比家鸡小的小许多,皮已发青,想必不久后就要孵化了。我不敢伸手去触摸。野鸡是极机敏的,若是蛋上沾染了异味,就会弃巢。想着不知所踪的野鸡,我原先的怒气消了。与我方才联想老虎、黑熊的情景相比,野鸡的胆识实在令人敬佩。
挖松茸得专注才行。拨开松茸菌盖上的落叶,我随手找了根树枝,用棍子往下撬动松软的腐殖质,撬出的腐殖质中有大量白色的菌丝。我取走松茸后,根据寻甸约定俗成的规矩,将挖出来的菌丝放回原处,盖上了腐殖质和落叶。
松茸菌盖上的花纹有红白两种。寻甸的乡民根据花纹色泽的差异,将其分别称为白花菌与红花菌。白花菌比红花菌珍贵,我捡到的也恰好是白花菌。我闻了一下,松茸散发出的气味儿悠远、纯然,不似人工合成的香水那般浓烈,我忍不住又多吸了几下。
我收好松茸,正欲往前走,不知从何处飞来了一只美人蜂,撞到了我的头。我大叫不好,连忙挥手驱赶。然而平素异常凶猛的美人蜂并未蛰我,径直钻进了一个树洞内。我走到树洞旁,见一个三指宽的土洞洞口爬着几只站岗的美人蜂。我便知道寻到蜂巢了。
将蜂巢筑于土层下的胡蜂,只需看其进出的频率,就能推断出蜂群的发展程度。其时,表弟离我不远,听到我的叫唤声,关切地在山里喊,问我怎么了。我说被吓到了。表弟闻讯急忙赶了过来。满头汗水的表弟见无事,看了一眼我,顺着我的目光看到了树洞内进出地美人蜂,顿时四目相对,笑语连连。
在杨房箐对面的山头,也有两个寻找野蜂的人,自听到我的叫喊声就不动了。因胡蜂是趋光性昆虫,夜间处理会更加安全。寻到蜂本是得做记号的,以免夜间找不到。但碍于对面山上的两个人,我们没做记号,只匆匆看了一眼周围的样貌便走了。我二人走的尽量不发出响声,不摇晃到树枝,以免被他们看到。
我和表弟走到村口,约好吃过晚饭便出发,以免夜长梦多。回到家,父亲与小妈已经做好了饭菜,只差煮我的野生菌了。父亲将我捡的菌子先进行了分类。云南每年都有食用野生菌中毒的人,但对于野生菌的食用却从未停止过。父亲将不能食用的野生菌丢弃,剩下的菌子用清水洗净,撕成若干片,烧油,加入调料,水烧开后放入菌子。煮菌汤不宜加入味精、耗油、鸡精等提鲜调料,否则会掩盖了菌子原有的香味儿。十五分钟后,一道鲜香的杂菌汤就做好了。
饭毕,鸟雀已在竹林内鸣叫。我带上手电去了表弟家。大舅早已准备了麦秆、锄头、布袋和防叮咬的手套。大舅驱车载着我和表弟一同前往杨房箐。
进入山中,我们凭借日间的记忆前行。由于夜间起雾,天太黑,加之植被过于繁密,我们彼此的距离不敢离得过远,只得在小范围内搜寻。本以为一切会很顺利,可我们寻了半个多小时,仍未发现美人蜂蜂巢所在的树桩。就在我们欲要放弃时,大舅让我们过去他那。我和表弟都以为他找到了。我问他是否找到了,他说没有,脸上却带着莫名的笑意。
大舅的手电一转,灯光照在了他头顶的一团水桶大小的白色东西。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个中华大胡蜂的蜂巢。大舅让我拿着他的手电。他爬到树上,将蛇皮口袋往蜂巢一套,蜂巢整个的落入袋内。我们收取中华大胡风的时候,表弟有些紧张,到别处解了个小手。不曾想他解的小手刚好淋在了美人蜂的洞口上。是可忍熟不可忍。敌人都打到家门口了,美人蜂自然要奋起反击,表弟被吓得抱头乱窜,回来时眼皮被蛰了一下。
表弟受伤,烧美人蜂的事儿自然落在了我与大舅身上。大舅用土封住蜂群进出的洞口,挥动锄头开始往下挖,土层里传出美人蜂愤怒地响声。我点燃麦秆焚烧不时挖出的美人蜂。不一会,蜂巢露出来了。大舅用燃烧着地麦秆放在蜂巢上一烧,即使再凶狠的美人蜂也只得饮恨而终。
烧完野蜂,收拾好工具,表弟捂着眼睛,我拿着锄头,大舅提着蛇皮口袋,走到路口便驱车回家了。
回至家中,尽管表弟的眼皮擦了药酒,可仍是肿胀的只剩一条缝,看上去不免生出笑意。大舅将蛇皮口袋放在铁盆,架在火上烤。一开始胡蜂飞舞的声音很大,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不多时就安静了。大舅将蜂巢掰开,抖落成年的野蜂,逐片取出蜂脾。蜂脾经过高温的烘烤,质地变脆,摘去“蛹盖”,向下一拍,白嫩的蜂蛹便掉了出来。
蜂蛹加上成年的胡蜂,一共六碗。舅母将洁净的胡蜂投入油锅。经过油炸,白嫩的蜂蛹转为金黄色,绵软的成年胡蜂变得干脆。出锅后,舅母撒上少许盐,便可以食用了。炸好的蜂蛹香脆可口,蛋白质的香味中经过回味,有一股淡淡的甜味。那夜,一家人都吃得极尽兴。唯有表弟例外。他对高蛋白过敏,按照以往的经验,只能数着吃,数量为十。当吃到第十只时,他的喉咙果然痒了,只得提早停著,坐在一旁抿唇看着。
前些时日,正值春季,一只虎头蜂误打误撞地飞入了我听课的教室。它无从知晓室外与室内还隔着一块透明的玻璃,频频在窗边“碰壁”,吓得班里的同学连忙躲避。好在靠窗的同学打开了窗户,它终是飞走了。对于无法掌握的事,我只能希冀。看着它逐渐飞远,我希望它能够抵达一处山重水复的天地,或是飞入我的梦境。
写于2021年5月15日四方小筑
作者简介:
陈刚,云南寻甸人,生于1999年,现就读于文山学院,为人文与传媒学院18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有作品发表于《散文选刊》《含笑花》《滇池》《寻甸民族文化》,曾获七届全国大学生野草文学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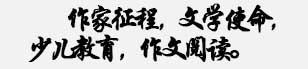
.jpg)